攝影:榴槤
他是民族學家,也是傳教士。
每走過一個地方,他一定要跟當地人學習,然後寫下來,用文字留下記錄。他延續了許多傳教士走過的路;在這條路上他認識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每一個人。他,努力記得自己經歷過的這一切。他變成了AMIS中的一位長老,當年輕人忘記自己的族名、遺失自己家族的族譜時,就會來求助於他。
他,從法國,緬甸,最後來到花蓮。他是巴斯克人安德烈.巴雷(André Pierre Marcel Bareigts),是上天的信使,是後來的「裴德神父」。
民族學與多元性的保存
在我們的這個時代,好像是一個缺少「記憶」的時代。不要說是天主教,宗教早已被很多人看作是被歷史淘汰的老古董。甚至是民族學家,當他們在追索一個族群的歷史、一種語言、一種文化的時候,也有很多人會質疑他們說:你又不是A族的人,研究A族的文化幹嘛?語言就只是用來溝通的,即使這個語言不再有人會講,走向消亡,又有什麼關係呢?研究這些有什麼用?試著去了解一個不是主流、而且或許會消失的語言文化,有什麼用?
可是,在我看來:如果沒辦法保住「多元性」,就不會有真正的尊重。裴德神父在故鄉、在緬甸、在花蓮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傾聽的行動,展現出真正的尊重。
這樣的尊重,難道我們這些在地人,和AMIS與其他族群,在同一個空間生長的人,反而無法展現嗎?即使我們無法每個人都去學習語言和研究文化,但至少:我們應當尊敬和援助這樣的用心。
文字的力量
當我在讀這本書時,讓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文字」在這一段歷史中的重要性。外來的傳教士,要進入花蓮向當地人傳福音。要怎麼做?首先就是編纂當地語言的辭典。「翻譯」成為一種連結,連結出身不同、語言不通的人;有一部分的人同時學會了兩種語言,成為兩族人之間的橋樑。先來的傳教士也透過這些文字(辭典、翻譯、資料),把他們的工作成果和教訓,傳遞給後來的傳教士知道。並且,AMIS的語言和文化,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被保存了不少。
當一個民族慢慢消失的時候:譬如說,年輕人都外出找工作,小孩被送到都市去受教育,而耆老慢慢凋零之後;我們不禁會問:那麼,保留這些「文字」下來,有什麼意義?
但是,只要這個民族還在的一天,一切都還是未定數。我們可能會損失一部分、某些部分;但我們可能透過還記得的部分、還在生活中的部分,藉著文字的輔助,再一次把它想起來。文字不必是一個結果,也可以是一個開端、一個過程,幫助我們找回過去的東西和思想新的東西,在不確定的命運中,與我們並肩作戰。
或許,就是這樣倚賴文字、與文字共同奮鬥的關係,讓作者王威智,想要把神父的故事記錄下來,寫出我們手上的這本《神父住海邊》。神父和作家,在他們生命追求的路途上,好像是兩種完全不相干的身分。但是,我在猜想:當王威智在讀神父的記錄時,那份記錄中訴說了為了留下故事,他如何四處遊走,探聽,耐心的與一個一個鄰居打交道。與每一個人說話。也許,在這其中:王威智也部分的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看見了那他已經成為、而依然嚮往的那個模樣。
傳說、神話的新篇章
本書的原名取作《以文字安頓——裴德神父與AIMS(阿美/朋友)的神話》。這個「神話」一詞,引領我們去發現在本書的結尾(〈MALO'〉),王威智蒐集了一些描述,讓我們看到、思想到:彷彿,裴德神父已經走進了AIMS的傳統裡,成為AIMS的傳說中,一個新而延續的篇章。
裴德神父的AIMS名字,取作MALO',意思是「坐下」。裴德說:
我就坐在這裡,不走了。
是的,他從此就留在花蓮、留在台灣;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鄰居。而在《神父住海邊》的最後四行,王威智帶著我們,去懷想神父在世時溫柔而自信的神采。有一次,當一個訪客詢問和AMIS文化相關的問題時,裴德神父講了很多:從部落的傳統是如何運作;部落之間互相聯繫與溝通的方式;以及在AMIS的傳統中,有哪些部分已經被教會採納和延續。最後,裴德神父對我們驕傲、歡喜的說:
我參與了這一切。
►相關書籍:蔚藍文化《神父住海邊:裴德與AMIS的故事》,王威智 著
►延伸閱讀:所有過去的,都是現在的記憶:藝術與書的懷舊未來式
►延伸閱讀:關於鯨豚、關於海洋、關於自然生態—《鯨豚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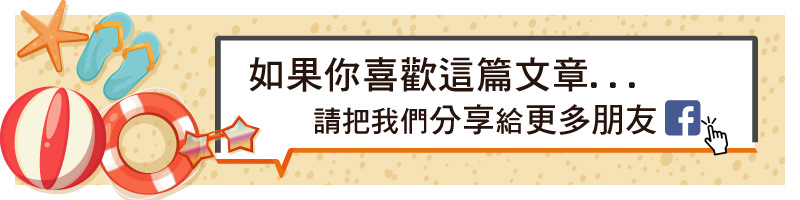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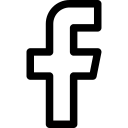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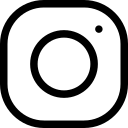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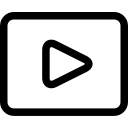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