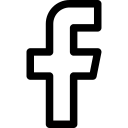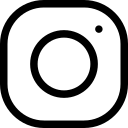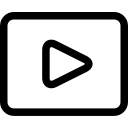Photo by Mykyta Martynenko on Unsplash
我不玩「猜猜猜」的遊戲了
「喪失記憶」,帶給失智症患者什麼樣的痛苦?
每次回家,小楊阿姨都會問媽媽,「你瞧瞧是誰回來啦?你認得她嗎?」陪媽媽在樓下散步時,阿姨們也會問我媽,「你知道我是誰嗎?」
人們總是喜歡問失智症患者「你知道我是誰嗎?」也許是出於一種好意,一種想要幫助對方保持或恢復記憶的努力。但是我最近在想,媽媽願意不願意人們老是這樣問她呢?對她來說,回答不出這些問題,甚至還要不斷被糾正「我不是你的姊姊,我是你的女兒」,會不會讓她備感沮喪和惱火呢?
我們其實無從知道,「喪失記憶」給失智症患者帶來的痛苦。雖然我們也都有過因為遺忘而帶來的尷尬、煩惱,但畢竟還能記住大多數賴以生存的事情:我是誰,我是誰的孩子、誰的妻子或丈夫、誰的父親或母親,我的家在哪裡,廁所在哪裡,怎樣刷牙、洗臉、吃飯……更別提我們還能記住這個世界上許多複雜的事情,因此可以工作、旅行、創作、讀書、觀影、歌唱、散步,享受朋友之誼和感官之樂。
●
一個人失去記憶,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提出「心流」理論(Flow)的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Flow: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中說,在古希臘神話裡,記憶女神是繆思之母。可見,古希臘人將記憶視為最古老的心靈技巧,並且是所有心靈技巧的基礎。沒有記憶,詩歌也好,後來的科學技術也好,統統不會出現。他還認為,「個人的歷史也是一樣,無法記憶的人,就喪失了以往積累的知識,無法建立意識的模式,也無從整頓心靈的秩序。」
失智症患者正是漸漸地「喪失了以往積累的知識」,這個喪失從不再能夠學習新東西開始。記得媽媽曾經想要一支手機,但妹妹送給她手機後,發現她從來不用,其實是因為媽媽已經學不會了。之後,失智症患者會逐漸逆向地忘記曾經懂得的、擁有的知識和技能,也許要一直倒退到嬰兒時代,不會說話,不會吃飯,不會大小便。
但似乎失憶帶來的麻煩還不僅僅是這些形而下層面的。如果失憶還會讓人「無法建立意識的模式,也無從整頓心靈的秩序」的話,這意味著老媽的內心也會變得混亂與迷茫。
藏東西和找東西,大概就是老媽處理混亂與迷茫的方法之一。
不過現在,老媽似乎已經玩膩了這個遊戲,又發明了一個新遊戲:我發現,有時她會像發現了什麼東西一樣,用手指從桌上、床上捏起某個細微之物(其實什麼都沒有),緊緊地捏著不鬆手。看到她的手捏得太緊,我只好說:「媽媽,給我吧,我幫你放起來。」於是,我就像演員一樣,假裝從她手裡拿過一樣東西,放在床頭櫃或書櫃上,然後告訴她,「媽媽,看,我放在這兒了。」
可能常人很難理解這些古怪的行為,不過我相信它們對老媽來說是有意義的。或許這都是她在記憶漸失之時,建立自己內心秩序的一種方法吧?說不定這些行為,能讓她感覺到自己還在控制著生活。
●
從另一個角度看,當病情愈來愈嚴重時,她似乎也愈來愈需要有人陪伴,只要沒有人和她說話,她就開始嘟嘟囔囔地發出生氣的聲音,並且拉下臉來。只有當有人可以坐下來聽她說那些聽不懂的話,或者拉著她的手在屋裡轉圈、跳舞時,她似乎才能平靜下來。
怪不得現象社會學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和盧克曼(N. Luckmann)認為,人得靠談話維持自身的感覺。俄羅斯學者巴赫汀(Bakhtin)更簡潔地表述為「存在即對話」,他認為,「存在就意味著進行對話的交際,對話結束之時,也是一切終結之時。」
當失智症患者記憶衰退,思維能力也隨之退化時,他們大概因為難以記住對方剛剛說過的話,也難以找到字眼(因為遺忘)組織起可以表達自己想法的話語,因此無法再進行有效的對話,甚至包括與自己的對話。當依靠對話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感,怎麼辦呢?也許生存的本能會讓他們去尋找他人,透過外部的力量來確認自己的存在和價值。這或許就是他們離不開人的真正原因。
●
記憶衰退帶給人的巨大衝擊和內心痛苦,哈佛大學神經科學博士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在她的小說《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中,做了極為生動的描述,雖然小說中的故事是虛構的,那個主角──哈佛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愛麗絲是虛構的。我想,如果作者真是一個失智症患者的話,根本就無法完成這樣一部作品,因為她會喪失描述自己感受的能力。正因為患者無法自我描述,所以他們的痛苦也不能真正地被我們知曉,更不要說被理解了。
這樣說來,他們不是一群非常非常孤獨的人嗎?他們如何處理那分孤獨?還有逐漸失去生存能力帶來的那分沮喪?還有面對一個愈來愈陌生的混亂世界的那分恐懼?還有漫漫長日卻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連電視都看不懂的那分無聊?還有叫不出對方名字時的那分尷尬?還有不會上廁所而尿濕自己的那分羞愧?
小說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愛麗絲(患者)誤將家門口的一小塊黑色圓形地毯當成了一個黑洞。一開始她害怕極了,以至於無法越過那個「黑洞」去到外面。後來,當她發現那是一塊鋪了許久的地毯時,她的憤怒爆發了,她用盡全力啪啪地去拍打地毯,直到又拖又拉把地毯扔到門外,自己筋疲力盡地倒在地上。
我想,那個突然爆發出來的憤怒裡,實在是包含了太多的挫敗、無助、羞愧和委屈,是記憶漸漸衰退中積累起來的情緒能量,是我們外人無法理解的心靈之痛。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還引用路易斯‧布紐爾(西班牙國寶級電影導演,曾執導《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的話說:「生命沒有記憶,就不能算是生命……記憶是我們的凝聚、理性、感情,甚至也是我們的行動。少了它,我們什麼也不是。」
失智症患者並非從一開始就喪失了所有的記憶,但到了臨終之時,他們還會擁有哪些記憶,恐怕就像宇宙中吞噬所有光的黑洞一樣,永遠不能為他人所知了。我願意相信,我情願相信,我想讓自己相信,在媽媽離開世界的時候,她還能擁有一種記憶,或者還能記住一種感覺,那就是愛──她還能記得她曾經被愛過!
●
患了失智症的人,實際上已經開始從自己的生命中抽身,向這個世界揮手告別,只是這個過程有時非常緩慢──這漫長的告別,或許是十年,或許是二十年,他們的眼神將在不知不覺中變得茫然、空洞,讓你感受到愈來愈遙遠,愈來愈縹緲、愈來愈疏離:人還在,身還在,但心魂是否還在?
我沒有回天之力。也許,我應該像龍應台那樣,每次去安養院看望媽媽,都這樣打招呼,「媽媽,我是你的女兒龍應台,我來看你了。」──而不是再問媽媽「我是誰」、「我是你姊姊,還是你女兒」。
按照巴赫汀的話說,對話具有「雙聲性」,你以為是在和她遊戲,但她聽到的可能是「你看,你叫不出我的名字吧?你連你的女兒都忘了」這種責備之聲。她沒有辦法組織起語言來告訴你,她是否喜歡被你這樣問,失去記憶也讓她失去了還擊之力。你無法確定她臉上的笑,是在努力掩飾自己的尷尬和無助,還是真的喜歡你和她玩這個遊戲。
算了吧,還是放下這個「猜猜猜」的遊戲,讓老媽的內心少一點無助和挫敗,讓她已經坍塌破碎的自我,能再囫圇著多維繫一些時間吧。
【照顧失智家人】
三個思考:
- 人們總是喜歡問失智症患者,「你知道我是誰嗎?」但是,失智者樂意老是被這樣問嗎?對他們來說,回答不出這個問題,甚至還要不斷被糾正如「我不是你姊姊,我是你女兒」,會不會讓他們備感沮喪和惱火呢?
- 不再能夠學習新事物,漸漸喪失以往積累的知識,這是否會導致他們內心變得混亂、迷茫?那麼,「藏東西」和「找東西」,是否為他們處理混亂與迷茫的一種方法?
- 他們如何處理那分不被知曉與理解的巨大孤獨?逐漸失去生存能力帶來的沮喪?面對世界愈來愈陌生和混亂而生的恐懼?漫漫長日卻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連電視都看不懂的無聊?叫不出對方名字時的尷尬?還有,不會上廁所而尿濕自己的那分羞愧?
本文轉載自寶瓶文化《我和我的失智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