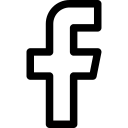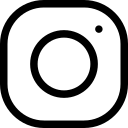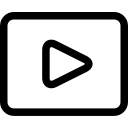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時速50公里的風吹雪,近8,000公尺的稀薄氧氣,隨時轟然襲擊的雪崩,險些一氧化碳中毒的驚心一瞬‧‧‧‧‧‧這是世界級的極限挑戰,貨真價實的俄羅斯輪盤,每一步,都是自己的思考、個人的判斷。
2023年5月20日,晚間9點整,準備出發衝頂
尼泊爾,道拉吉里峰第三營,海拔7,250公尺
塞進四人的壅擠三人帳裡,充斥著尼龍布料窸窣的摩擦、咿歪咿歪的睡墊擠壓、鉤環們清脆的金屬碰撞,還有四人因移動與對話而發出的喘息。
這一刻,是今年登頂道拉吉里峰的第二個好天氣窗口,一旦錯過,就是明年再來。
五月底開始,從印度洋吹來、飽含水氣的季風將無情地把這裡變成暴雪與暴雨的悽苦絕境,驅逐地表任何會呼吸的物體,卻也帶給整個南亞滋養生命的甘泉,就像印度教三大主神的濕婆神一樣,矛盾地執掌毀滅與再生。
.jpg)
▲ 出發登頂的阿果
「OK,走囉!」
拉開歪斜的帳門,阿果與元植身著連身羽絨衣,踩著巨大的雙重靴,鑽過堆滿裝備的擁擠前庭,沒入不見五指、微風流動、氣溫不到負15度的刺骨黑夜。
阿果本名呂忠翰,是台灣頂尖的登山家,截至2023年5月,無氧攀登了7座8,000公尺高峰,為台灣之最。
他跟上早一步出帳的張元植(阿果的全人實驗中學學弟,台灣頂尖登山家),朝著自己2021與2019年未竟的目標──海拔8,176公尺的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展開了最後推進。
道拉吉里(Dhaulagiri)在尼泊爾語中的意思,是「白色的山」。
在歪歪斜斜的帳篷裡目送他們離去的,是從未爬過8,000公尺大山的我,與我的雪巴嚮導拉可帕(Lakpa)。
這時,第三營的其他六位攀登者也一同出發了,加上阿果、元植一共八人,是今年攀登道拉吉里的倒數第二支隊伍。
留在這傾斜、凹凸不平、講話稍快一點就會喘、海拔超過7,000公尺的帳篷裡的,就只剩下我們兩個。
前庭的雪反射著耀眼白光,我趴著仰望阿果、元植緩緩走遠的身影,心中滿溢著祝福與期待。
期待他們帶著這次我放棄的登頂心願,繼續開創台灣無氧攀登的新篇章,並一圓阿果兩次未竟的峰頂夢,讓台灣人距離無氧完成十四座八千米高峰的世界殿堂又更近一步。
▌ 海拔8,000米的最「高」享受
沒多久,成列的頭燈與鉤環碰撞聲遠去,第三營回復一片寧靜,只有我們的帳篷依然發散著明黃的光,不時被風吹來的冰晶刮得沙沙作響。
「先生,你要麵包嗎?」拉可帕的英文不太好,只能用單字與短句,搭配簡單的尼泊爾語和客戶進行溝通。
「不用喔,謝謝!可以幫我煮點水嗎?」
由於我們兩個都穿著米其林寶寶似的連身羽絨裝,在帳內交換位置很不方便,我拜託他幫我融雪取水,自己則拿出鈦鍋,打開從台灣帶來的「台酒花雕酸菜牛肉麵」,將凍硬的油包與真空包放進胸前口袋軟化,並把瓦斯和爐頭組裝好,準備親手烹調能振奮心神的家鄉味。
帶著甘甜牛肉湯與花雕酒香的煙霧,在零下的帳篷裡冉冉上升,堆積在帳篷穹頂,就像一週前繚繞在道拉吉里山頂周遭的雲霧。
這是用融雪煮成的思鄉情,是親朋好友們的祝福,也是味蕾的頂級盛宴,令人回味無窮。
八千米死亡禁區邊緣的這一碗泡麵,毫無疑問是我人生之中,最「高」級的享受。
尤其這次連鍋組、瓦斯都是自己背上來的,那是一種自主的成就感、發自內在的肯定與滿足,無可取代。
吮著筷子、舔去嘴角的最後一滴,從尼泊爾第二大城波卡拉出發整整兩個月來,在這條冰河上的日子一幕幕閃過腦海:峽谷健行、受困大雪、西北稜下的基地營、八千米新路線的開拓,傳統路的商業攀登和跨國情誼,將我推到當下身處的人生新高,並在這裡扎實地睡上一晚。
撇開八千米,台灣爬過7,000公尺高峰的人不少,但曾在7,000公尺以上好好睡過覺的人,屈指可數。
▌ 命運促使我選擇了撤退
一切都是那麼地奇幻、不可思議。
但話又說回來,我的狀況這麼好,為什麼不緊抓這萬事俱備的窗口,跟著阿果、元植一起衝頂,站上世界第七高峰的山巔呢?
一直到2023年為止,台灣爬過八千米的人,依然是鳳毛麟角般的稀少,道拉吉里峰更只有兩個台灣人登頂過,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啊!
在台灣登山,常聽到「撤退需要勇氣」。而此刻,我的回答是:
「撤退是一種選擇的自由,命運帶著我選擇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