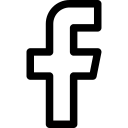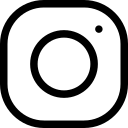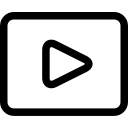圖片來源:canva圖庫
24歲,成為「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操盤手之一,日交易量超過170兆台幣;27歲,毅然決然急流勇退,成為改革體制的倡議者,提出富人稅;直到今天,他仍投身於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積極出現在紀錄片或各大媒體,試著挑戰一場贏不了的比賽。一起看蓋瑞.史蒂文生不平凡的人生‧‧‧‧‧‧
從許多方面來說,我天生就應該是交易員。
我長大的那條街盡頭是一排高大的回收子母車組成的凹牆。它和一盞路燈、一根電線桿彼此相距四公尺,形成一組完美的即興球門柱。
如果你站在兩根柱子之間,往後退十大步,抬頭凝望它們的正上方,金絲雀碼頭最高的摩天大樓的燈光會從遠處透過那堵高牆,對著你眨眼。
小時候,我會在放學之後,穿著破爛的校鞋和我哥哥的舊校服,在漫長的傍晚繞著球門柱,裡裡外外、一趟又一趟的踢著破舊的軟式安全足球。媽媽來叫我回家吃飯時,我總會習慣性的回頭望著那棟對我眨眼的摩天大樓。它在我眼中是一種全新生活的象徵。
我和那些閃爍金光、高聳的資本主義寺廟共享的,可不只是東倫敦的街道,還有其他東西,某種共同的信念。
關於錢的信念。關於渴望的信念。
▌ 一枚硬幣,對小時候的史蒂文生來說卻是價值不斐
金錢的重要性,以及我家並不富裕的認知,從小就深深的刻在我的骨頭裡。
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爸媽給我一枚一英鎊硬幣,叫我去埃索加油站買檸檬汁。在路上,我弄丟那枚硬幣。它不見了。
我還記得為了那枚一英鎊硬幣找了好久好久,甚至鑽進汽車底下爬行,在排水溝裡亂挖,感覺我找了好幾個小時才放棄,兩手空空的回家,淚流滿面。雖然事實上我大概只找了三十分鐘。
不過我想,當你還是個孩子時,三十分鐘是一段很長的時間,而一英鎊則是很多很多錢。
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失去過對金錢的熱愛。雖然,現在回想起來,我不確定是不是應該用「愛」這個字。
也許,尤其當我還是小孩子,我覺得它更可能是一種恐懼。
無論我對錢抱持的是恐懼、熱愛或渴望,隨著我長大,那種情緒也就愈來愈強烈,驅使我不停的去追逐那些我從未擁有過的英磅。
十二歲,我開始在學校賣廉價糖果給同學;十三歲,我開始一年三百六十四天的派送報紙,賺取每週十三英鎊的工資。到了十六歲,我在高中的銷售業務變得更激進、更有利可圖,卻也更不正當。
但這些小打小鬧從來都不是我的真正目標。每天晚上,太陽下山後,我總會抬頭凝望那些在街道盡頭對我眨眼的摩天大樓。
然而,從現實面來說,我並非天生就會成為交易員。因為這些方面,不管過去或現在,對個人成就而言都非常重要。
▌ 身懷雄心壯志的年輕男孩多不勝數‧‧‧‧‧‧
因為在東倫敦摩天大樓的陰影中,在路燈柱和汽車周圍踢著破舊足球,滿懷渴望、野心勃勃的年輕男孩很多、很多。
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很聰明,許多人都意志堅定,幾乎每個人都願意犧牲一切,只為了能夠繫上領帶、戴上袖扣,走進那些高大、閃亮的金錢巨塔。
可是在走進閃亮摩天大樓的交易大廳,在每年賺取數百萬英鎊之後仍以東倫敦港區人自居的年輕人卻再也聽不到來自米爾沃爾區和堡區、斯特普尼區和麥爾安德區、沙德韋爾區和波普拉區的熟悉口音。
我知道,因為我曾經在其中一個交易大廳工作過。曾經有人對我的口音感到好奇,問我是哪裡來的,而他才剛從牛津大學畢業。
金絲雀碼頭的花旗銀行大樓共有四十二層。在我進入花旗的二〇〇六年,它是英國並列第二高的建築。
二〇〇七年的某一天,我決定登上大樓樓頂看看風景如何,順便看看我能否從那裡看到我的家。
花旗銀行中心頂樓僅供會議和活動使用。換句話說,當沒人用它時,整層樓都是空的。鋪滿鬆軟細緻藍色地毯的地板,宛如一個遼闊而連綿的國度,四周則是厚厚的落地玻璃圈成的圍牆。
我無聲的走過地毯,來到窗前,卻發現我無法看到我的家。
從花旗銀行中心的四十二樓看不到東倫敦,只能看到匯豐銀行大樓的四十二樓。東倫敦野心勃勃的孩子們仰望在他們房屋上投下巨大陰影的摩天大樓,可是摩天大樓卻不會看向他們。它們只會互相看著彼此。
這是我如何從在摩天大樓陰影下踢足球、在學校賣糖果的所有孩子裡脫穎而出,在花旗銀行交易大廳找到一份工作的故事。
這是一個關於我如何成為花旗銀行全球最賺錢的交易員的故事。這也是一個關於我為什麼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選擇離開的故事。
「生活就是生活,遊戲就是遊戲。」
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弄懂那是什麼意思。我還在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們能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