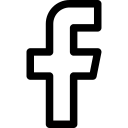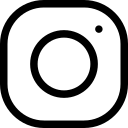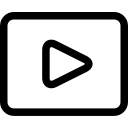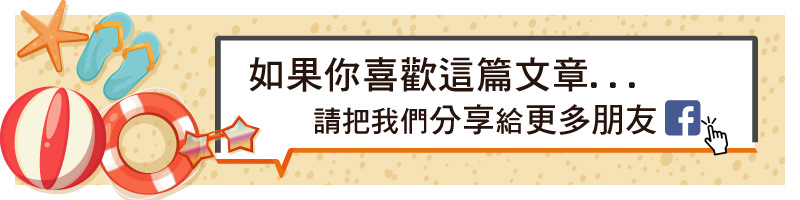我想,如今他的死亡方式,
又未嘗不是另一個
帶領我與其他餘下的家人,
又或者是正在讀這本書的人,
前往另一個生命學習路程的老師?
《修復事典》裡,江佩津以「物」、「情緒」、「生活」三大塊面闡述母親自殺後,他面對物品,開心以及悲傷,與「被留下來」—分成有親人自殺的上半輩子,和被留下來的延續—的人生樣貌。
他描述他的母親曾多次囑咐,說他已經簽署了器官捐贈、大體捐贈同意書。
「活著的時候希望能夠為世界所用、所需要,倘若死去,也希望自己的死亡能至少擁有一些意義。」江佩津寫道。
不過當他前去查詢自殺者能否捐贈大體時,他發現是不行的,相關的網頁上寫著:「我們不接受自殺結束生命者,因為不珍惜自己的人無法教導醫學生尊重生命。」
江佩津回憶母親生前的努力,只能結語:無論如何,他不像是完全放棄、不愛惜生命的人。如果母親是遭逢意外,總之是以其他的方式離開人生,也許他就會成為在醫學院學生中的大體老師,教導未來的醫生們生命這一堂課。
「我相信,」江佩津接續記錄:「無論是怎麼樣的死亡,都能夠給我們許多未曾想過的事物,應該要是如此才是。」
S的告別,讓我想要成為溫柔負千斤的糞金龜
搭車去參加S的告別式的時候,是微陰的清晨,我對S其實沒有什麼印象,我知道他,但他應該不曉得我是誰。
S選擇從高樓一躍而下的方式結束他的人生,周遭的許多人無論親近或疏遠,都受到驚愕與悲傷地重磅襲擊。朋友們告訴我,說他們總覺得,如果自己多加留心,這一切或許可以避免。但我卻在朋友的惋惜聲中,感到憤怒逐漸升溫,我告訴他們,這些都是後話。
可能是感覺整件事很遙遠吧,搭車的時候還不太知道情緒是怎樣的。但到了告別式現場,看著會場棚內S的親朋好友,一直到致詞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滿溢的罪咎和愧歉感,源源不絕的自喉頭深處湧上。
那個我沒說過幾句話的S,在朋友的口中是一個溫暖愛笑的人,還有點幽默,懂得關心別人。從一個接一個陸續的致詞,在會場裡共同的哀悼空氣中,S的形象逐漸變得具體起來,像是黏土被塑型;原本在我心中模樣朦朧的他,其實是有溫度的,活生生的,許多人牽掛惦記的,善良的人啊。
但是S來到新的生活環境以後,似乎很不適應,他的個性有了極大的轉變,這一點,似乎是我們這些新的疏遠的人應該知道的?我不曉得什麼事讓S變了這麼多,我驚訝於我一直以來以為奇異的S,其實是在笑聲擁戴中成長。
如果我沒辦法想像,如果我錯愕,如果我憤怒與罪惡感叢生,那些深愛S的人們,該如何去排解他們錯綜複雜的情緒?
後來,我暗暗立誓要成為把世界上的悲傷推成巨大圓球的糞金龜,把心臟的鼓動,用盡力氣傳遞給鄰近的人。更後來的後來,當我被悲傷的圓球壓倒在原地,許多人接力聽見我的聲音,把我從圓球底下拉出來。
我仍在學習,人生的奧義和做人的道理,每經過一件事,我的心臟都變得更柔軟又剛強。S,是你讓我學會這些。
先走的人,留待我們之後相見
我不責怪那些已經先離開的人,
事實上,我也沒有資格責怪任何人,
那是他們的人生,
根本輪不到他人來評論,
而我要做的也只是把自己的人生
繼續過下去罷了,
無論那是多麼費力、疲憊,
但也是珍貴的,我的人生。
江佩津的母親燒炭自殺,他敘述自己可以看著相關關鍵字「燒炭」、「凶宅」,甚至不拒絕聚眾烤肉的局,他說一年之內可以做到這樣的事,「令他意外」。
但是他也追述:「這並不代表我已經好了,我知道,人生不像是電視劇或是電視動漫,可以在看似轉好的部分就收尾,而是在那樣的轉折過後依舊持續下去,可能往上、往下、持平,總之就是那麼一回事。」
在《修復事典》裡,透過追憶和分享、採訪相似經歷的自殺者遺族,江佩津用平實堅定的口吻,細書每個物品遺留的溫度,和被留下來的掙扎和恐懼。
「至少,我現在比較不害怕黑暗了」。在一次線上共同分享裡,江佩津說。然後獲得了零星的回憶,讓他覺得不那麼孤單。
點點的星火,可以環繞每個失落的人,使迷失的心中點滿燈火;希望活著的時候,我們能在有能力的時候選擇善良放光,到了離開的時候,好好抱抱那些先行離開的人。到時候,無論是要笑著哭,或是委屈大抱怨自己一直以來都很難受,都有很多時間。
珍貴的你的、我的人生,期許都能盡興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