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canva圖庫
這裡是大阪梅田。
大阪站是每天吞吐量高達八十五萬人的重要門戶。只要由此邁開腳步,走向西日本規模最大的商業區,巨大的百貨公司和洗鍊的辦公大樓、櫛比鱗次的餐飲店,就會夾雜著熱氣與混沌、還有不可思議的調和感,在眼前敞開。高層大樓一棟接一棟地陸續興建,街道景觀現在依然時刻在改變。
二〇一一年一月的深夜。
一對母女就在那個街區,漫無目的地徘徊。
「要去哪裡?」
就讀國一的北川幸(化名)跟著媽媽美雪(化名),漫步在街道上。小幸並不知道媽媽的目的地。
百貨公司、錢湯、餐廳,已全數走過一遍。美雪邊喃喃自語,邊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街道來回。路上行人對美雪的舉動投以訝異的眼神,那視線讓小幸深惡痛絕。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回家呢?究竟要去哪裡?好想快點回家——
回到家時已過半夜十二點,明天還要上學的說……
「這種生活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要崩潰了。」
小幸內心充滿絕望。直到多年以後,她才慢慢瞭解,這種漫無目標的徘徊,或許是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母親以她自己的方式在和女兒互動。
小幸是大阪市出生、長大,土生土長的大阪人。
幼稚園時,父母協議分居,她跟著母親,兩人一起住在市區的公寓大廈。發病前的美雪,興趣廣泛、喜歡往外跑。也積極加入小幸小學的媽媽排球隊,勤於練習。對小幸而言,與自己感情要好的美雪,是她暗自引以為傲的母親。
▌ 曾經引以為傲的母親,卻開始變得不大尋常‧‧‧‧‧‧
沒想到,等到小幸升上小學高年級後,美雪突然變得常窩在家裡睡覺、足不出戶。
明顯感到不對勁,則是小幸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美雪會用小到聽不見的微弱聲音,不斷自言自語、看著虛無的空中傻笑。叫她,她也不應。看起來就像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小幸心想「媽媽是把我當空氣嗎?」這種倍感困惑的日子,愈來愈多。
小小年紀的小幸,當然不會有思覺失調症的相關知識。家裡又只有兩人相依為命,所以也沒有商量的對象。
小幸上國中以後,美雪變本加厲,行為舉止變得更加無法預測。連原本極拿手的廚藝、洗衣、打掃,也都碰也不碰了。自言自語的音量愈來愈大。聲音大到連小幸在自己房裡都聽得見。
她不想聽媽媽那不知所云的喃喃自語。只好關在房間裡面,戴上耳機,一直聽音樂,做自己的事。
雖然被媽媽漠視的感覺很強烈,但媽媽有時也會突然跟她攀談。
每當小幸放學回家,媽媽就會拋下一句「走囉!」,然後就帶著她到超市、錢湯或餐廳。去的地方形形色色,不到目的地不會知道要去哪裡。
雖然心裡其實不想出門,卻不敢違抗臉色兇惡的媽媽。說起來,打從以前,美雪就很會搜尋想去的店或咖啡館。所以看來似乎是先有個方向,這才帶著小幸前往。
她們的去處雖以梅田等繁華熱鬧的商業區居多,但有時也會去冷冷清清、什麼都沒有的郊外。
有天,美雪帶她來到位於市營地鐵終點站的錢湯。那是個看似只有在地人才會去的地方。美雪漫無目的地帶著她,在那個住宅區走了將近一個小時。
有天則是冷不防地,小幸突然就被要求坐上計程車。問美雪要去哪裡,她只簡短地說「和歌山」。在美雪的指示下,計程車載著她們來到距離大阪約兩百公里的和歌山縣串本町。抵達後,也沒什麼計畫,只是無所事事地信步而行。小幸沉默不語,媽媽則是邊走邊自言自語。
美雪沒先預訂飯店,卻恰巧有房間可以入住,可說是唯一慶幸的事。然而,完全沒有那種家庭旅行會有的開心好玩的事。
美雪極厭惡小幸走在自己後面。只准她走在前面或旁邊。小幸一定得隨時在媽媽視線範圍內。搭手扶梯時,也總是被要求站在媽媽前面。而這也讓小幸壓力山大。
在外面時,只要一進餐廳,美雪一定單方面幫小幸點餐,完全不顧她的意願。「吃這個!」
對於心情沮喪、毫無食慾的小幸而言,這只能說是酷刑。即便如此,因為媽媽一定會催逼她吃,所以也只能順從。
兩人總是深夜才回到家。那之後小幸才能寫功課、打理媽媽不再碰的洗衣工作。
好不容易上床睡覺時,已是凌晨四點左右。
兩人一起去超市。代替詞不達意的媽媽,和收銀台店員溝通的是小幸。美雪簡直就像購物成癮般,大肆採購同一商品。裝著用不到的雜貨、食品、還有垃圾的大塑膠袋,堆滿了家裡走廊。美雪不做飯的時候,小幸就從那裡面拿出速食食品或零食來充飢果腹。
美雪也控制她的服裝,許多天都強迫小幸穿著她規定的運動衣或運動褲。
荒蕪的家。沒洗的衣服。小幸每每在浴室一待,就是將近兩個小時,彷彿被什麼附身似地拚命刷洗身體。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實難忍受「骯髒的自己」。美雪的行為舉止令她無從理解。
美雪已不再洗衣,卻不知何故,有著用酒精消毒家中所有物品的癖好。小幸的制服也全是那個味道。每次教室裡有人說「怎麼好像有股臭味?」,小幸頓時緊張兮兮,擔心自己露餡,幸而沒被同學發現,這才鬆了口氣。緊接著心裡一股對媽媽的怒氣不禁油然升起。她好想放聲大罵,叫媽媽不要為所欲為!
在深夜打理家事和洗澡時間太長等因素影響下,小幸常處於睡眠不足的狀態。上課打瞌睡的情況也隨之增加。她變得課業跟不上進度,成績也往下掉。
即使親戚一再催促美雪去醫院,她還是頑固抗拒,表示自己沒事。雖然不解何以變成這樣,但是隨著時間流逝,小幸也逐漸接受跟判若兩人的媽媽,視為生活理所當然的一部份。
打從孩提時候,小幸就常被說「聰明伶俐」。在美雪的事情上,周遭大人也常關心,表示:「你真的很努力」。但是,小幸其實對這句話厭惡至極。
大人們或許想表達讚美之意……但她卻覺得彷彿只想要用一句話打發自己承受的一切似的,她感到既氣憤又傷心。
▌ 校園生活,反而成了小幸僅有的避風港
唯一讓她放鬆的地方是學校。家中的一切可以在與同學談笑之間暫時忘卻,她也幾乎不曾在朋友圈中談論母親美雪。「突然跟朋友說起家人的煩惱,朋友應該會不知所措吧」。她希望,唯有學校,一定要營造成「開朗的場域」,因而內心暗自決定,絕不在同學面前曝露自己陰暗的一面。
美雪對小幸的束縛愈來愈多。
她異常討厭小幸單獨外出。早上準備上學時,美雪會突然兇巴巴地對她說「今天不必去學校」—這樣的情況,一個月會有個幾天。不過是打算去附近的便利商店,卻才打開玄關大門,美雪就會從裡面飛也似地衝過來,生氣責問「你要去哪裡?」
因為這樣,所以即使朋友約她出遊,她也總是回絕。
也有朋友不放棄地一再邀她,讓她非常過意不去。所以她也曾輕描淡寫地稍微跟這些同學說明原委。
可以穿想穿的衣服、自由外出的同儕,讓她倍感羨慕。「為什麼只有我不行?」。有一次,她終於忍不住騙媽媽說有社團活動,會晚一點回家,然後和朋友去了。國中時期和朋友一起出遊的回憶,就只有這麼一次。
只要放學晚點回家,美雪就會用尖銳的語氣質問她去了哪裡。連要順道去個藥妝店,都得想方設法。為免因為提購物袋,被美雪發現自己回家路上沒有直接回家,她只得把買來的物品藏在書包裡面。流感流行的冬天,全班停課,小幸也被傳染、發高燒,美雪卻不准她去醫院。
不過,媽媽倒是一定會出席中學的學校活動。在老師、家長、學生三方面談的親師會席上,她仍舊嘟嘟噥噥地自言自語。小幸只好拚命幫媽媽圓話改口,蒙混過關。
小幸開始偷偷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用公共電話打電話給住在附近的外婆,商量媽媽的事。擔心外孫女的外婆,常常代替再也無法做飯的美雪,幫小幸準備便當。
外婆有一本記錄小幸求援的手帳。
▌ 「我真的不行了,救救我吧!」小幸崩潰地吶喊著‧‧‧‧‧‧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三天連假期間,小幸被帶著到處去,去了百貨公司、天然溫泉、吃飯。直到半夜十二點前才回家。」
「真夠受的了。美雪不但自言自語、傻笑、強逼小幸吃飯,而且嗓門還很大。」
「二月二十四日小幸沒上學。我去拜託她導師協助不要讓她請假。」
除此之外,根據外婆的筆記,小幸所處的狀況大致如下:
不讓她上學、不讓她唸書、也不讓她和朋友交流、完全不顧她本人的想法、漠視、帶她到處走直到半夜十二點左右。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這一天發生的事,小幸記得一清二楚。
半夜十一點,美雪跟平常一樣,把她帶到梅田的親子餐廳,並擅自點了牛排。小幸雖覺無奈,也只得開吃,但是當她把肉送到嘴邊時,卻突然一陣不適、噁心想吐。
即便如此,眼前的美雪仍硬生生地強迫她趕快吃。
就在這時,長期緊繃的心弦突然喀擦一聲斷了。
「我真的不行了。救救我吧。」
小幸瞞著媽媽,操作手機,寄郵件給分居的爸爸和親戚。過不久,爸爸就過來接小幸。並大發雷霆地斥責了媽媽一頓。其後,外婆雖前往區公所、兒童商談所諮詢,這些單位卻沒有任何作為,只一味地說「應該送母親去住院治療」。小幸心想:就是因為要說服媽媽住院很難,才會去諮詢呀!
小幸也曾忍無可忍,不假思索地衝著美雪說「噁心」,這種時候,她總是心痛又難受。
「媽媽只信任我,我卻這樣對她。」
對於曾經和自己那麼親密的媽媽,她一方面想親近、一方面卻又想抗拒,兩種感情交錯,讓她糾結不已。
就在小幸即將國中畢業前,親戚齊聚一堂,說服美雪住院治療。那天早上,幾位媽媽的親人來到家裡,把掙扎抗拒的美雪架進車內,送到醫院。不忍看到無力反抗、硬被帶走的美雪身影,小幸刻意在那個時間離家外出。但是,她的心裡鬆了口氣,慶幸自己總算可以解脫了,也是不爭的事實。
美雪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小幸一直到這時候才知道媽媽的病名。於是,她開始針對這個疾病,研讀相關書籍。
上高中後,小幸搬到外婆家,也重新獲得自由。
她終於有自己的時間,可以讀書、參加社團活動、和同學玩在一起。美雪雖一再重複住院、出院的過程,病狀倒也逐漸改善,可以再度一起生活。小幸彷彿要彌補失去的時光般用功讀書,順利考上大學。
有一天,當她翻看國中畢業紀念冊時,目光突然停留在一張全班團體照上。相片裡面沒有她。
「啊!」我那天沒上學呀。
記者曾問二〇二〇年初以來幾度受訪的小幸以下的問題:回顧過往,對當時媽媽的行為舉止有何看法?
「現在想來會覺得,也許她是因為無法操持家務,所以想要透過外食、錢湯來善盡身為母親的責任吧。因為她是個凡事都力求完美的人。」
小幸已經長大成人,朋友建議她應該過自己的生活。然而,小幸卻一直無法擺脫「有我就有媽媽,兩人一組」的感覺。
「那感覺就像是,雖然想和媽媽聊點什麼,卻又沒什麼好說的。因為我們原本關係就蠻親近的。沒想到疾病卻突然找上媽媽,有種硬被拆散了的感覺。如果沒有這個疾病,感覺我們應該就是一對平凡無奇、感情要好的母女。」
時至今日,小幸還是只要一踏進親子餐廳,就滿心厭惡。也很怕和別人一起吃飯。因為她總是會想起當時的自己。不過,她並非感到怨恨。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誰也沒錯,而且想預防也無從預防。只能說碰到了沒辦法,就是想開、接受。」
二〇二〇年春天,考上研究所的小幸,開始過著一個人在外租屋的生活。搬離老家是小幸自己的決定。因為她覺得,離開媽媽是一個契機,讓她能夠思考自己的未來,還有家族應有的樣貌。
時值新冠疫情肆虐,學校課程大約連續一年都是線上進行。雖然跟她原先描繪的學生生活有些出入,不過,她開始打工,也談了戀愛。「一開始雖對離家在外有些害怕,不過現在已大致習慣了。」
她在研究所主要鑽研的主題是兒少照顧者。
即便從照顧家人的工作中解脫,應該有很多人的心靈依然深受影響吧。她想把焦點放在孤立無援的人們身上,成為他們的助力。
►延伸閱讀:知道太少,做得不夠!搶救卡在人生起跑點的「年輕照顧者」
►延伸閱讀:震驚日本社會!毒親高壓管教女兒崩潰:「我打倒怪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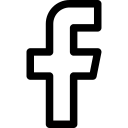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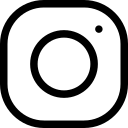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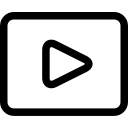



%E8%BA%AB%E7%82%BA%E5%AE%88%E8%AD%B7%E8%80%85%E7%9A%84%E5%B0%91%E5%B9%B4%E5%80%91_%E7%AB%8B%E9%AB%94%E6%9B%B8%E5%B0%81%2B%E6%9B%B8%E8%85%B0_300dpi.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