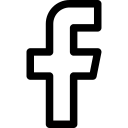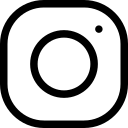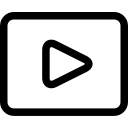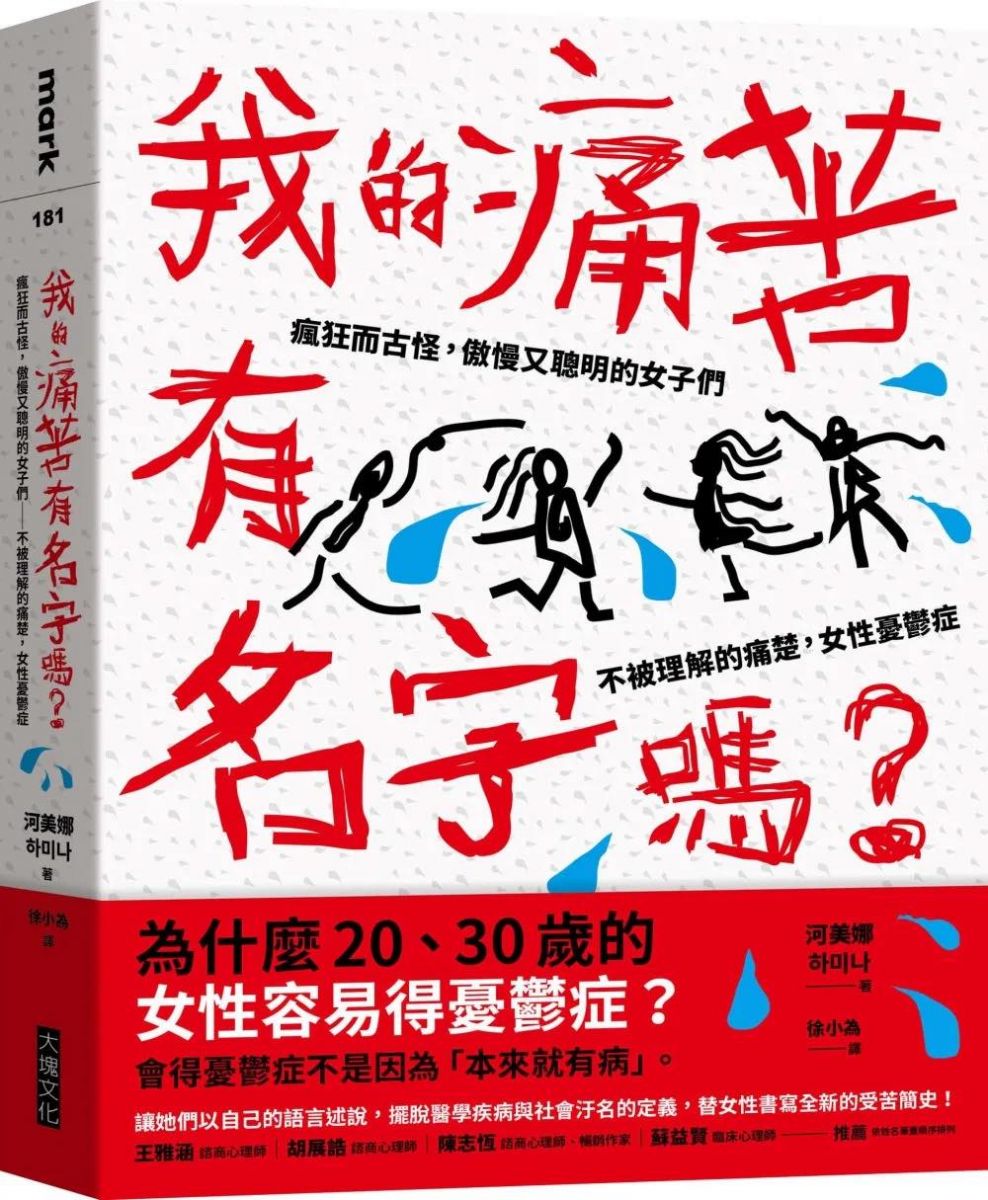十六世紀的藥學課;來源:Wellcome Library
精神疾病有不同於身體疾病的特殊性。憂鬱症的診斷中不會有明確的生物性測試。懷孕時,我們會透過驗孕棒或超音波檢查確認懷孕與否;診斷高血壓時需要測量血壓,並以量出來的數值決定是否罹患高血壓,糖尿病也一樣。然而憂鬱症患者的體內並不存在這樣的生物性指標——即所謂的生物標記(biomarker)。雖然有憂鬱症自我檢測工具或DSM診斷守則,但這些全都是以外顯的症狀構成的量表。
也就是說,因為一開始就不存在足以判別罹患精神疾病與否的生物標記,吃藥的時候必須要相信才行。就是雖然沒有明確證據,但我相信自己得了憂鬱症的相信。
或許有人會認為血清素、正腎上腺素、多巴胺等具情緒調節效果的神經傳導物質,或者大腦的特定部分是一種生物標記,但這樣的生物性條件只能說明精神疾病的其中一小部分。不只是情緒障礙,對於人格障礙、行動障礙等大部分的精神科障礙而言,「大腦毀壞」並不是生病的結果,而更接近是過程。究竟是因為神經傳導物質不平衡導致憂鬱,或者是因為憂鬱才使得神經傳導物質變得不平衡的,幾乎難以判斷。
副作用轉正為精神科藥物
精神科藥物是怎樣被拿來作精神疾病治療的呢?藥的歷史跟診斷的歷史一樣粗糙,越往深處挖掘越覺荒唐。現在我們所用的藥,不知道有多少都是偶然發現的。不是在確切釐清作用機制後才使用,而是經驗上知道該藥對特定症狀有效果,於是便用在治療上面。
比方對思覺失調症狀有絕佳效果、最早的精神病藥物——氯丙嗪(托拉靈),其來源是被作為染色劑使用的化合物亞甲藍(methylene blue)。而早期抗憂鬱藥物伊米帕明(imipramine,常見商品名為妥富腦)也是從被稱為”summer blue”或”sky blue”的染料而來。單胺氧化脢是血清素、多巴胺等神經傳導物質氧化後分解而成的酵素,而單胺氧化脢抑制劑(MAO inhibitor)原本則是被用於火箭燃料的物質。它們全都是為了作為鎮靜劑、麻醉劑,或用於心臟手術的新藥等其他目的而被開發出來,偶然發現能產生其他效果後,才被拿來當成精神科藥物使用。也就是說,藥先被開發出來,等到發現意料之外的用途時,才以原有的資訊為背景以演繹方式進行研究。就像過去許多藥物都被發現原本期待以外的用途一樣,我們現在使用的藥,也會以不同於原本意圖的方式作用在我們身上,我們把這稱之為副作用。
鋰鹽的運用
拿鋰鹽的歷史舉個例子。鋰是組成宇宙的元素,比人類更早就存在於宇宙之中。雖然鋰元素本身性質並不安定,但對於吃藥的人而言則能帶來寧靜的平穩感受。鋰鹽不同於其他人工合成的精神科藥物,是自然狀態下就能在石頭裡發現的物質。
而鋰鹽被發現能作為躁鬱症藥物的過程則稍微有點荒唐。鋰鹽從19世紀中葉開始被作為精神疾病治療的處方藥。然而早期的鋰鹽治療法很快就被淡忘,直到1949年,才又被澳洲精神科醫師約翰.凱德(John Frederick Joseph Cade)拿來治療躁症。但他的實驗同樣是在錯誤的科學基礎之下進行的。
當時的醫生認為酸性尿(acidic urine)是所有重病的原因。凱德收集多位精神病患者的尿液注入天竺鼠的腹腔反覆實驗,想找出引發精神疾病的誘因。被注入濃縮尿液樣本的天竺鼠們每次都全數死亡。凱德推測使天竺鼠死亡的主因是尿酸(uric acid),為了使不溶於水的尿酸溶解,他在尿液樣本中加了鋰鹽(lithium salt)。接著把這份樣本注入天竺鼠體內之後,出現了驚人的結果。天竺鼠並沒有死,反而意識清醒且狀態非常平穩。凱德為了證明鋰鹽的效果,便用自己身體進行實驗,在這之後又將患者作為實驗對象。鋰鹽做為躁鬱症藥物的效果,就是像這樣將精神病患的尿液注入天竺鼠體內才被發現的,非常出人意料。
鋰鹽在精神醫學史上留下了一筆大功,拯救了許多病人。它不僅歷史悠久,且以化學性質來說既單純又有效,更重要的是和其他精神科藥物比起來,無須經過人工合成就能在自然環境下取得。但關於鋰鹽究竟如何影響人類所感受到的情緒,我們依然無從得知。也只有極少數的學者研究鋰鹽在腦內如何作用。羅倫.斯萊特將其原因解釋為「鋰鹽不具收益性」。她認為鋰鹽是「最能展現精神醫學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利益之間關係有多緊密的藥」,並批評就算已經有了對很多人都有顯著效果的鋰鹽,製藥公司仍然為了專利與獲益埋頭開發新藥。
受資本主義影響的藥物開發
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被開發問世,就需要資金。精神科藥物也一樣。就算發現了新的藥效,製藥公司為了開發新藥,就必須確保商品的市場性。憂鬱症的藥想賣得好,就需要憂鬱症患者;思覺失調的藥想賣得好,就需要思覺失調患者。製藥公司衡量完潛在患者的數量之後,判斷其具有市場性才會決定開發藥物。開發完藥物之後,再以具攻擊性的行銷方式積極宣揚該疾病,並「製造出」潛在的患者。反過來說,就算發現藥物的新用途,如果判斷不具市場價值的話,也就不會再繼續開發下去。
雖然人們認為疾病及其療法單純屬於科學的產物,且必須得是單純的科學產物才行,但現實並非如此。疾病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性的產物,藥也一樣。想吃藥的話,我們就必須定義某些特定狀態屬於「生病」。讓一種藥物進入我們的生命之中,就等於是對理解痛苦的文化本身做出改變。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我的痛苦有名字嗎?:瘋狂而古怪,傲慢又聰明的女子們--不被理解的痛楚,女性憂鬱症》,河美娜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