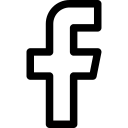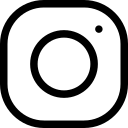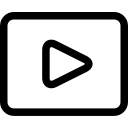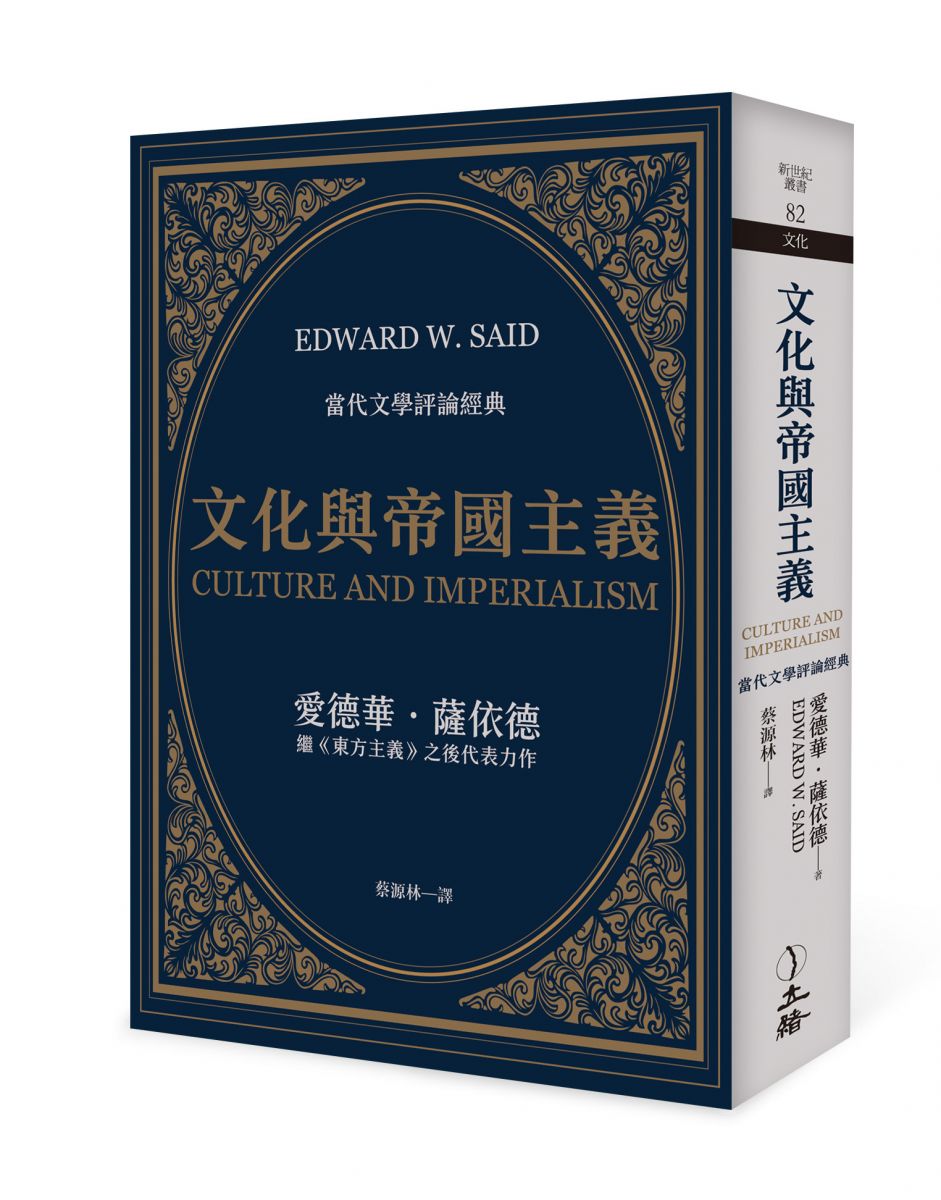Hot Pies,與英國帝國主義相關的漫畫,繪於1879年。繪者:John Tenniel。
《文化與帝國主義》並不是一本對讀者友善的書。我分別用兩種方式閱讀過本書:將其視為一首尾連貫的著作,從頭到尾的一次性讀過;將各章分別視為對特定議題的討論,為每部分的每個章節做摘要。第一種閱讀方式是痛苦的,薩依德在四個部分處理的內容之繁雜、引用作者之多、涉及時間之廣泛,使我難以辨識究竟他想說些什麼。第二種閱讀方式是順暢但不明確的,薩依德常用之對比技巧,讓每一句話與段落之間似乎都能存在足以寫成簡潔筆記的內容,但各個章節乃至各個部份之間的關聯對我而言仍然不明確。
在我朋友提供的一本關於殖民理論之著作中,則提到了另一個問題: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試圖將殖民主義建構為一種於個別歷史事實之上的、廣泛指稱各類型殖民活動之模型,但這個模型的內容卻又依賴於個別歷史事實所指的對象(殖民地官員、帝國主義者、砲艦外交),使其充滿曖昧乃至於自相矛盾。綜合而言,這本書對於任何一個試圖了解薩依德的人而言,不管在陳述結構或陳述內容上,都是容易讓人迷失或不知所謂的。
但且讓我轉換視角,以薩依德在書中運用的「對位式閱讀」來更好的了解這本書。這本書的作者是誰?是一個出生自英佔巴勒斯坦地區、擁有阿拉伯基督教信仰,在英屬埃及設立的殖民地學校學習母國語言,並在戰後移居至全球影響力第一國家——美國——的人。陳述至此,我好像還是沒有說清楚他「究竟是誰」,不過是將他在時間中擁有的不同標記一一列舉。但此時有個問題值得思考:
一、他何以擁有這些標籤?
這顯然不是什麼困難的問題。翻閱他的戶籍資料、通信紀錄、出入境證明,我們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知道這些標籤在特定時間的依附與剝除。然而我們也可以設想另一個人,他同樣擁有這些標籤——英佔巴勒斯坦出身、阿拉伯基督教信徒、於英屬埃及受教育、移居美國——但並非我們所知的「愛德華.薩依德」。是什麼讓前者與後者有所不同?難道只是因為前者在某個時間點做出了(對前者來說)應該的選擇,使其遠離另一種可能性?究竟是什麼讓應當隨機發生(包含擁有什麼標籤)的事件密集的結合在一起,在特定時間、地區對特定的人發生作用,使前者成為愛德華.薩依德、(無數的)後者什麼也不是?這需要我們思考第二個問題。
二、他應該擁有這些標籤嗎?
這似乎也不是困難的問題。翻閱歷史書籍、信件或口述記錄,隨處可以看見「英法兩國占領蘇伊士運河」、「英法代管巴勒斯坦與黎巴嫩」、「美國成為戰後全球頂尖強國」這類型的論述。但為何我不將「英屬埃及」稱為「被非本地人軍事占領、實行官僚體系統治的土地」?為何我不將「美國」稱為「歐洲移民以武力拓展其統治區域的大陸」?是什麼讓某些或某個答案,成為在無數可能性中被挑選、被普遍化,彷彿說出它就能實現什麼魔法(猶如美國之於「美國夢」)?這又促使我們思考的更深入,即第三個問題。
三、是什麼使某些標籤在陳述時成為一種應然(ought to)?
至此,我們終於觸及本書的核心。薩依德的答案很簡單: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實踐不只是某些人拿著槍擊潰反抗、在「特別的時刻」宣讀命令、在每年的某些時刻要你繳稅,也包含對人認識世界的能力進行改造(modification)。以薩依德在〈帝國主義的享樂〉一章中所引的《金姆》原文為例:
……這種人(英國警察)才能維護正義。他們通曉這塊土地與習俗。其他人(帝國新培訓的官員)則全部剛從歐洲過來,由白種女人哺育長大,從書本學習我們的話,竟比瘟疫更可怕(註1)。註1:薩依德《文化與帝國主義》,頁271。原文引自Kipling, 《Kim》, p242
這是一位印度老寡婦對英國警察的評價。這段話暗示了三個帝國主義的實踐:
1.「土著」是無法維持自身生活的。唯有象徵秩序的帝國代表(此處為警察)才能行使對不符秩序者之懲罰的權力。
2.帝國相較其統治的「土著」更了解後者自身。
3.這兩種狀態是無條件(超越時間、地區)有效的。
3.尤為重要。如前述,帝國意圖建立的不只是對某些土地、人群在某個時間的控制,而是將這種控制在被統治者的心中樹立為一種無條件的、永恆有效的情境,讓其以此為基礎認識世界。帝國成了被統治者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對「因野蠻而被帝國開化」和「因帝國開化而野蠻不再」兩個概念的討論中,刻意去除了時間的因素,使失去時間的歷史事實彷彿成為了真理。
但只認知到帝國主義是問題的可能答案並不夠,薩依德更想要獲得可能的解答。如果在書中第一、二部分中我們看見的是目標明確的薩依德,第三、第四部份的則是身處夾縫難以抉擇的薩依德。本書初版的90年代,正是美國在伊拉克作戰勝利、帝國主義隱然勢起的年代,但不論非洲、阿拉伯半島或中亞等地,大量的區域政權皆以民族主義這個「帝國的自我認同」做為去殖民化的首要工具。
換言之,在薩依德目光所及的世界,帝國主義在任何一個他所擁有的標籤所在地仍然持續進行著。他的分析正確的認知到這點:那些在「為帝國主義辯護」與「為民族主義辯護」之間試圖走出第三條路的人,若不是被其中一方攻擊(如魯西迪因《撒旦詩篇》遭伊朗當局追殺)、便是尚不成氣候(儘管賤民研究的理念是薩依德本人讚賞的)。
若把目光放回2023年的台灣,面對「雙語國家」的推行、「台語羅馬字」的常見認知、以及「電資醫牙」獨大的局勢,再回頭檢視過去400年來這座島做為「土著」被看待的歷史,《文化與帝國主義》的研究方法仍然值得被更多人細加品味、運用,乃至於在思想上真正走入「後殖民」的階段。
全文經 葉元淯 授權轉載